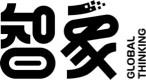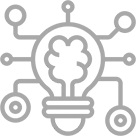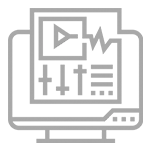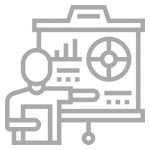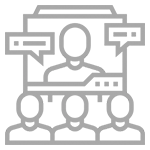2021年,残酷的现实狠狠给了万宝科技一巴掌。
“那一年,我们亏了八千多万人民币,一下回到解放前。”万宝科技董事长薛栋语气平静地讲述这段经历时,背后的数字却显得惊心动魄。
疫情带来的居家办公红利骤然消退,加之汇率、原材料、海运三座大山压顶,他仓库里还有几十万张椅子,压力大得“整个团队都喘不过气”。
在“中国椅业之乡”浙江安吉,薛栋的经历并非个例。这里的工厂们曾无比安全地隐身在全球家具产业链的后台,为海外品牌默默代工。
如今,他们被时代洪流裹挟着,被迫冲向了前台,要直接面对全球消费者。这是一条走向全球市场的诱人赛道,也是一段布满荆棘的艰难旅程。
“逼”出来的转型
在浙江省西北部,杭嘉湖平原的腹地,安吉这个常住人口仅60万的小县城,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椅都”。全国每三把椅子中就有一把来自安吉,全球一半的椅子都与这里息息相关。
这里汇聚了数百家家具制造企业,孕育了恒林、永艺、中源等上市企业,形成了从面料、海绵、五金、塑粉到整椅制造的完整产业链。正是这片深厚的产业土壤,成为了“薛栋们”远征全球的底气与起点。
“以前是客户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赚的就是一点工钱。”一位安吉的工厂老板形容,传统代工模式就是在价值链的最末端挣扎。
利润空间被无限压缩。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订单的不确定性,大客户一抽单,工厂马上就得停工。
安吉的工厂主们开始意识到,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一条腿是维持传统代工(B2B)业务,保证现金流;另一条腿必须迈出去,通过亚马逊等平台做跨境零售(B2C),搏一个未来。
转型的冲动,首先来自客户的“倒逼”。薛栋发现,从2012年开始,一些跨境卖家客户下单越来越频繁,单量越来越大,“我们扩产能的速度已经赶不上他们下订单的速度”。替别人代工,不如自己做品牌。
然而,从B端到C端,绝非开一家亚马逊店铺那么简单。这意味着一场从思维、组织到商业模式的全方位重构。
“最难的坑,我们都踩过了”
“让我们的B端同事去了解一下C端怎么做,根本行不通。”薛栋发现,做惯了大订单、长周期生产的工厂团队,完全无法理解跨境电商小批量、快反应的节奏。2016年,他不得不在杭州独立组建全新的跨境团队。
人才是核心痛点。来自福建的德诺林业跨境电商合伙人熊友聪也有同感:“一个运营总监可能要八十万、一百万,工厂的厂长一年才二三十万。”在安吉本地,成熟的跨境电商运营人才凤毛麟角。
最初,工厂们习惯性地把为B端生产的产品直接搬到线上,结果惨不忍睹。
“我们很多卖不掉,积压了很多库存,一下亏了很多。”薛栋的初次试水以失败告终。问题出在哪?脱离市场需求的盲目铺货必然失败。
真正的转机来自一次破釜沉舟的美国之行。2018年,薛栋带着团队在美国的商超里泡了十几天。在机场,他看到一个身材丰腴的女性,突然问同事:“她坐得下我们的椅子吗?”
答案是否定的。这个瞬间刺痛了他。
回国后,他立刻组织研发重磅椅,专为承重300磅以上的消费者设计。用薛栋的话说,就是这把椅子,让万宝在亚马逊上“瞬间超过了一些过去卖得很好的卖家”,有一款产品甚至冲到大类排名第八。
这种冲突不仅体现在人才和产品上,更深刻地体现在对“成本”的理解上。
工厂思维看重的是生产成本。一个零件省5毛钱,一年一百万件就能省50万,这是工厂最关注的。但跨境思维看重的是全链路成本和‘机会成本。一个产品因为省了5毛钱的零件导致差评率上升1%,引发的售后、退货、流量下滑和Listing权重下降所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超50万。
而这种认知差,需要无数次踩坑和算总账才能弥合。C端生意的复杂逻辑,逼迫着传统工厂老板们走出舒适区。
对于动辄几十公斤的大件家具,物流是命门,也是最大的成本黑洞。
“物流的坑也踩过特别多。”97年出生的新生代卖家、杭州霖生家居创始人宋易霖回忆创业初期,所有数得上号的物流企业他都试过。大件家具的超长、超重附加费极高,尾程配送体验直接影响退货率。
如果说选品是大脑,那么物流就是跨境卖家的双腿。而对于大件家具来说,这双腿常常是戴着镣铐在跳舞。
有卖家透露,大件家具的物流成本能占到售价的30%甚至更高。尺寸重量是第一个命门。亚马逊和快递公司对超重、超长、超围长的商品有极其复杂的附加费体系。有时产品重量只是增加一点点,但因为它进入了另一个计费区间,物流成本就可能呈跳涨式上升。
包装是第二个命门。安吉的卖家们在这上面交足了学费。“我们早期以为国内运输的包装足够结实了,结果到了海上漂一个月,再经过海外仓的辗转,到客户手里可能已经散了架。”宋易霖回忆。
现在,他们必须进行严格的摔箱测试,将包装好的产品从一定高度进行多角度抛摔,内部产品无损才算合格。
海外仓储是第三个命门。自建仓管理复杂,第三方仓服务参差不齐。旺季时,找不到仓库收货、上架速度慢、错发漏发等问题频出,直接影响销售节奏和客户体验。
因此,像薛栋那样通过极致的产品设计,将一个货柜的装货量从168套提升到300套,带来的成本优势是碾压性的。
“一个柜子可以装300套,别人只能装138-168套。”薛栋将物流效率做到了极致,这也构成了万宝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别人降价10%就没利润了,我还有。”
解决工贸一体的终极难题
如何让前端灵敏的“贸易大脑”和后端沉稳的“制造身躯”协同起来,是这场转型的核心。
产品经理这个角色变得至关重要。
“这个产品经理不是生产经理,也不是销售经理,它是连接运营公司跟工厂端的角色。”熊友聪强调,“有的大卖,产品经理甚至比运营总监的待遇还高。”
他需要懂材料、懂结构、懂工厂流程,还要懂得C端的包装、说明书应该与B端有何不同。他是翻译官,也是指挥官,将市场的需求精准地翻译成生产的指令。
另一方面,工厂必须为C端开辟“特区”。小单快反是对传统工厂模式的最大挑战。
“要求工厂对我们的配合是很零碎化的,”熊友聪说,“比如半个月、一个月生产50件或100件出来。有N个50件、100件去测试,很快就能测出来未来1000件、1万件体量的产品。”
这要求工厂必须有专门的打样车间和灵活的生产线,愿意为未来的可能性付出当下的成本。这考验的不仅是能力,更是老板的决心和眼光。
在这场艰难的转型中,平台的力量不容忽视。亚马逊等跨境电商平台推出的产业带加速器项目,成为了传统工厂的“新手教程”。
对于安吉的工厂而言,平台提供的不仅是流量,更是一套如何做C端生意的“操作系统”。例如,商机探测器(Product Opportunity Explorer) 和选品指南针(Marketplace Product Guidance) 这类工具,利用AI技术将海外的消费趋势和未被满足的需求翻译成工厂能理解的选品建议。
比如“户外阳台小型、可折叠藤编沙发”需求增速远高于供给,并建议“增加防水功能,目标价格区间定在300-500美金”。这种精准的洞察,让习惯于凭经验生产的工厂老板们第一次真正“看见”了终端消费者在想什么。
从“拼价格”到“卷价值”
当越来越多的家具工厂涌入跨境赛道,内卷不可避免。唯一的出路是跳出价格战的泥潭,走向价值竞争。
价值体现在极致的产品适配。来自福建、主营日本市场的捷安信运营总监有田分享,他们发现日本公寓楼梯狭窄,消费者不愿网购大件床。于是他们聚焦开发97cm宽的单人床和120cm宽的半双人床,精准切中了75%的市场需求。
价值也体现在绿色环保。 全球市场对可持续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的木材全部是可追溯的,符合FSC森林认证。”熊友聪介绍。
使用水性胶水、无甲醛涂料、可降解包装,不再是为了合规,而是成了打入高端市场的敲门砖。
价值最终将通过品牌来沉淀。“我们中国没有几家是真正做品牌的,大家都是在普通卖货。”熊友聪认为,品牌的突破点可以在于服务,“大家都卷价格,何不去卷服务呢?”比如在北美提供大家具的一站式配送甚至安装服务。
如今的安吉,跨境电商的星星之火已呈燎原之势。宋易霖这样的年轻一代,凭借着对亚马逊的熟悉和无畏的冲劲,快速崛起;薛栋这样的“厂一代”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完成了惊险的一跃。
从后台的代工车间,到直面全球消费者的亚马逊前台,这场远征注定漫长而艰难。它考验的不仅是产品、运营或资金,更是打破旧我的勇气和重塑新我的智慧。
安吉的椅子,正在全球市场上,为自己争取一把名副其实的“交椅”。